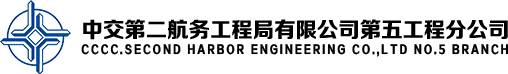中國人過中秋,賞月、談月、吟月、詠月早已成為一種習(xí)慣。而每當(dāng)論及“月詩”“月詞”,則必以東坡為范。蘇東坡對月之陰晴圓缺,人之悲歡離合的立足點(diǎn)甚高,看得更為透徹,將其一貫豪放的風(fēng)格展露無余。故北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中有“中秋詞,自東坡《水調(diào)歌頭》一出,余詞盡廢”一說??梢?,東坡樂觀與豁達(dá)為世人所推崇。
然而,東坡始終只有一個,關(guān)于月缺月圓,在大多數(shù)古代文人眼中,卻幾近滿眼的悲苦離殤。
從白居易的“三五夜中新月色,二千里外故人心”到李曾伯的“問他年,憶取今宵,人如許、月如許”;從辛棄疾的“可憐今夕月,向何處,去悠悠?”到熊孺登的“一年只有今宵月,盡上江樓獨(dú)病眠”。在他們眼中,月亮不管如何皎潔,如何光亮,如何唯美,如何圓滿,多多少少總帶有幾分憂思幾分愁苦,或思念家鄉(xiāng),或盼望團(tuán)圓,或牽念友人。如今,月亮在我們心中似乎也成了一切愁苦寄托的“恩許之地”。
古人對月的鐘愛,并以月寄情,不同于20世紀(jì)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(xué)。古人的愁苦在主觀上是文人對憂思的感受遠(yuǎn)遠(yuǎn)高于對美好生活的體味,而在客觀上則源于通訊不便、交通閉塞緩慢,方式單調(diào),以及頻發(fā)的戰(zhàn)亂。而如今,交通、通訊之發(fā)達(dá)亦非昔日可比,生活壓力固然尚存,但以機(jī)器生產(chǎn)機(jī)器,對人力的取代已擴(kuò)展到越來越多的領(lǐng)域,生活條件好得多,以筆者淺見,不必過多融入愁苦的情緒之中。月光畢竟還是陽光,而陽光不止天上有,心里也要多存留幾分。正如東坡所言:“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,此事古難全。”團(tuán)圓之夜未團(tuán)圓,好比月之“陰缺”,難全其美,何不樂觀豁達(dá),承襲東坡遺風(fēng)?
據(jù)說,在古希臘神話中,月亮女神的名字叫阿爾忒彌斯,她是太陽神阿波羅的孿生妹妹,同時她也是狩獵女神。月球的天文符號好像彎彎的月牙兒,象征著阿爾忒彌斯的神弓。所以,不論是在科學(xué)上說,還是在神話傳說中,月亮始終與太陽息息相關(guān),太陽照不到的夜里,月亮就是光明,而不是愁苦。
月亮在中秋之時,實(shí)現(xiàn)了自身的完滿與皎潔。像月亮一樣團(tuán)團(tuán)圓圓,是我們心中的向往,對千千萬萬工地上的人來說,似乎很遙遠(yuǎn),而事實(shí)并非完全如此。團(tuán)圓分為幾種:時間上的團(tuán)圓、空間上的團(tuán)圓和心理上的團(tuán)圓。月亮象征團(tuán)圓,月餅也象征團(tuán)圓,眾人齊心,奮戰(zhàn)在一線,苦樂共享,何嘗不是一種更有深度和層次的團(tuán)圓?空間上不能團(tuán)圓,但時間上和心理上的重合、團(tuán)圓不是千上萬水阻隔得了的。
時代的變遷,讓中秋團(tuán)圓的意義更加深遠(yuǎn)和豐富,而且越來越具有教育意義。中秋團(tuán)圓告訴人們的,早已不僅僅局限于私人感情,而是與時代緊密相連。在某種意義上說,中秋節(jié)的每一個毛孔中都細(xì)吐著新時代的氣息。中秋團(tuán)圓也不再局限于客體面對面與心靈共振的結(jié)合。或許在將來,“原子化個人”式的團(tuán)圓會演變?yōu)?ldquo;共同體理想”式的團(tuán)圓。因?yàn)樯鐣桨l(fā)達(dá),人不是越慵懶,而是越勤奮,越懂得奉獻(xiàn)于集體。即使從社會歷史發(fā)展的角度講,這也是一種高尚和無私,它在思想和實(shí)踐上推動了歷史的進(jìn)步!
“但愿人長久,千里共嬋娟。”相信時間和空間的局限,會在“神交”中得以劃破!